
【TMHT-005】由回憶混蛋A小隊所提出,現場演出的新可能性 ── 「當靈魂樂化作手語,直至以手語傳遞出靈魂樂」
■ 篇名:由回憶混蛋A小隊所提出,現場演出的新可能性 ── 「當靈魂樂化作手語,直至以手語傳遞出靈魂樂」
■ 翻号:#TMHT - 005
■ 文字總量:10427 字
■ 翻譯 / 校稿:多名尼特君 / 愛迪生發明的是黑暗
■ 發行商:隨時可能會腰斬的翻譯組
■ 圖片 / 原文出處:音楽ナタリー
✐ 翻譯史大斗

2021 年 11 月 27 日,思い出野郎Aチーム (回憶混蛋 A 小隊,台灣樂迷多稱之為野郎、野郎小隊、小隊等等,本篇後面則以「野郎」代稱全名)於新木場 USEN STUDIO-COAST 舉行了樂團史上最大規模的《SOUL PICNIC 2021》演出。
實際上,這場已是樂團睽違 1 年 9 個月的有觀眾現場演出,由 Fukaishi Norio、沼澤成毅、FANFAN(ファンファン)、asuka ando、YAYA子 等支援樂手加入行列,並以一場感動且出色的演出成功收尾。
這天還有加入另外一項特別嘗試的作法,那便是為了將歌詞傳遞給聾者們,因而邀請手語翻譯一起參與演出。在日本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狀況下,在這天演出前樂團究竟做了哪些事前準備工作呢。我們訪問了在樂團中擔任主唱的高橋一、當天參與手語隊一員的 PENKO(ペン子),以及擔任樂團經紀人的仲原達彥三人。
INTERVIEW : 高橋一、PENKO(ペン子)

一般來說,說到手語翻譯,腦中浮現的便是在電視畫面角落直立不動揮舞著雙手的畫面吧。不過,這天的翻譯團隊將這個認知給徹底顛覆了。她們隨著野郎所演奏出的節奏與訊息,彷彿產生共振般,一邊搖動身軀、舞動,以及運用包含臉部表情甚至是全身各個部位,同時進行手語翻譯。而我從沒見過像這樣的情景,手語簡直就像是一種樂器又或是合聲般的存在。我想不論是在會場亦或是在線上直播中看到的人,對這個畫面都會感到十分震驚吧。
而身為這次手語翻譯團隊的核心人物,便是想將音樂與手語做連結,曾有過 the HIATUS 於武道館等經驗,也持續不斷進行各種手語推廣活動的 PENKO 桑,在她的提議下,手語派遣中心〈TA-net〉(NPO Theatre Accessibility network)的成員們也加入其中,為野郎當天的演出完成了出色的翻譯任務。
不過,「將歌詞以手語來傳遞」說起來簡單,實際要去實踐這件事的過程經歷了那些艱苦的部份呢?到底要怎麼樣才有辦法做到像那樣一邊開心地邊跳邊以手語翻譯呢?我們所不知的事情還多著呢。這些疑問,對於做為野郎的團長以及經手所有歌曲的作詞者,並將歌詞化為手語傳遞委託給翻譯的 MAKOICHI(補充:MAKOICHI = マコイチ = 高橋一) 同樣存在著疑問。
在那場感動人心的演出結束幾天後,在擇日進行了這場 MAKOICHI × PENKO 的對談中,首次揭露當靈魂樂化作手語,直至以手語傳遞出靈魂樂的過程。而這一連串的發現,或許很有可能會改變我們對音樂的理解也說不定。
訪談&文字:松永良平
攝影:中嶋翔(訪談部分) / 廣田達也(現場表演部分)
✦ 真正想表達的內容,不知道為何有一種逆推回去般漸漸被整理起來的不可思議感
── 幾天前(11/27)在 STUDIO COAST 舉行的單獨演出〈SOUL PICNIC 2021〉中最為搶眼的,便是作為特別演出登場的手語翻譯了。從最早登場的 PENKO 桑帶來的舞蹈手語、手語成員們也彷彿是樂團成員的團隊感,以及最後在〈愚蠢的好麻吉〉(アホな友達)時,全員笑著舞動身軀並使用手語進行「默唱」的部份,可以說是一場讓心中淚如雨下般的感動演出!今天,便是希望可以透過訪問野郎的 MAKOICHI(高橋一)桑、PENKO 桑兩人,來了解從最初至實現這場演出所經歷的過程與辛苦之處。另外,也想透過這篇取材,來聽聽兩位對於當天演出的一些回憶。
MAKOICHI(高橋一,後以「M」做對話代稱):在 2019 年的第三專輯《Share the Light》之後,我們就有在反省:「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只放了一些政治性的歌在裡面?」。作為一個多數受眾,對自身帶著毫無自覺的加害性,以及如果僅僅只是旁觀的話,那便會產生另一種袒護放任其滋長的責任,對於這些部分,我感覺我們沒有太多著墨。如果在今後的歌詞創作中考慮到這些部分,我希望不僅是以歌曲的形式來呈現,若是將這股動力轉換成實際行動的話,那就太好了。
所以在這次睽違 1 年 9 個月的演出之際,便浮現了「不如找手語翻譯如何?」的點子出來。原本只是由經紀人 TATTSU 君(仲原達彦)提出邀請各個支援樂手,組成特別編制的想法。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像是 Kendrick Lamar 還有饒舌歌手 Chance the Rapper 等人都有在演唱會上帶上手語翻譯之類的,那時聽到就覺得好棒、這也太讚了吧。但後來仔細一想:「為什麼我們在一開始就沒有想到要把手語翻譯納入演出呢?」,如果是以一種藉由實踐的過程來學習,進而達成改變的意義上來說,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何嘗不來試看看呢。在樂團內的討論也像是「那不是聽起來蠻讚的嗎?」的輕鬆氛圍開始。雖說如此,但真的是完全沒在想實際上要花上多少心力來進行這部分。手語翻譯的安排交給 TATTSU 君之後,這過程其實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是怎麼變成由 PENKO 桑負責的。

PENKO(後以「P」做對話代稱):首先,在有「野郎的演出有附帶手語」的公告時,當下我完全沒收到任何一點消息。在那之後,是看了公告的朋友跟我說:「野郎的演出好像有附翻譯耶,好厲害喔!」,我看了一下 Twitter 之後才看到類似「目前徵集各種意見中」的推文。剛開始的時候,仲原桑當時還在詢問其他的手語翻譯派遣人員對吧?
仲原:是的沒錯。不過,一開始詢問的團體在聽到我們的需求後,對於要在娛樂產業進行手語翻譯這件事並沒有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導致對話一直停滯不前。而那同時也發出了「目前徵集各種意見中」的公告,想說如果可以從這推文獲得什麼有用的資訊那就太好了。然後便與她(PENKO 桑)搭上線了。
P:我也是想說或許我可以幫得上忙,就在 IG 上面發了一個「雖然我不知道是由誰來負責手語的部分,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個很棒的嘗試,我會為你們加油打氣!」附帶 tag 的貼文之後,就在當晚仲原桑便敲來:「請讓我和妳談談!」的訊息。
仲原:我看了一下 PENKO 桑的帳號,因為偶然發現有共同認識的人在其中,便覺得如果是她的話應該是可以討論相關事宜。
P:我在 2014 年的 the HIATUS 的演出中有被請去做手語翻譯。在那之後也跟許多人談過「我想要做像這樣的手語活動」的相關話題,但卻完全獲得不到下一次演出的機會。所以這次可以說是抱著一個「也許是個機會?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擔任你們的手語翻譯一職」的心情來聯絡看看。
── 拜讀了 PENKO 桑寫在 note 中的內容,原本有在「澀谷WWW」Live House 工作過一段時間嗎?
P:當時是擔任開場的工作人員(オープニングスタッフ)。而後我目標要成為一位手語翻譯員的契機,是因為 2011 年發生的的東日本大地震。震災之後,Live House 有好一段時間的排程都是空的,雖說我都在家處於待命狀態,但在那段時期我所尊敬的樂手們都到東北支援搬運物資。當時感到自己的無力時,在政府的新聞發佈會上看到手語翻譯師們的活動,我立刻萌生了「就是這個!」的想法。如果我學會手語,我不就可以用他們的語言向他們說「你還好嗎?」就在隔年進入了專門學校,並於 2014 年取得了手語翻譯師的專業資格。
仲原:和 WWW 的工作人員有共同的認識的人。因為有這層連結,以及聽了她開始進行手語翻譯的契機後,便覺得可以安心將這份工作託付給她來做了呢。
M:你們剛剛說的那個,不是一個超重要的話題嗎!?
仲原:在與 PENKO 桑討論的過程中,她向我介紹了一個專注於娛樂領域的手語派遣中心〈TA-net〉。因為與 PENKO 桑搭上線的時間點已經蠻晚的,所以要以一個人去完全負責 2 小時的現場演出,在準備時間上完全不夠。不過,如果是以〈TA-net〉一起協力負責的形式來進行,由〈TA-net〉派遣 4 位,再加上 PENKO 桑共 5 位成員的話,就勉強趕得上準備工作。
M:在決定手語演出的人員名單的同時,也開始進行將歌詞翻成手語的討論。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也才終於了解到「原來手語是這麼一回事啊」。每一句歌詞都會有著「這部分是這樣解釋的嗎?」,以及「這邊呈現的是怎麼樣的風景呢?」等討論。在我們的歌曲當中,會在有限的字數中選擇帶有雙關的詞來進行譜寫,關於這部分要如何以手語來進行表現呢,在與他們互傳郵件的討論過程中,逐漸反思自己在歌詞中真正想傳達的內容。這種反思反而讓我感受到一股不可思議的整理感,即便像是自己也不知道在寫什麼的部分,在手語的領域中,如果不講清楚的話就無法進行表達。舉例來說,像是由 PENKO 桑進行翻譯的〈奏響同一個夜〉(同じ夜を鳴らす)當中,有段唱出:「街道上的樹木斷斷續續地遮擋著街上的光(街路樹がコマ切れにする街のあかり)」,PENKO 桑就會問我像是「其中提到的路樹是從下往上看呢?還是從遠處觀看呢?」這樣的問題呢。

P:稍微補充說明的話,就知道日本大致上分為兩種主要的手語類型。而我們使用這種被稱之為「日本手語」的方式,不論是翻譯「日語」或是「英語」的方式都一樣,都是透過手勢加上半身的肢體動作來傳遞「意思」的一種「語言」。而另外一種則有像是「日語對應手語(日本語対応手話)」的形式,這個也被稱之為「手指日語(手指日本語)」,將一字一句作為視覺輔助般的存在,手語的動作則會根據日文的「發音」進行對應。
※原文編輯備註 :「日本手語」是一種以手勢為基礎的語言,將「意思」透過手語「翻譯」成表達方式,作為一種獨立的「語言」來傳達。相對地,「日語對應手語(日本語対応手話)」則是將「日語」裡的「一字一句」按照日文的語順直接「轉換」成手語,作為視覺上的輔助來傳達。
仲原:雖說我一開始自己講著想要加入手語翻譯,但我真的是沒做足功課,一開始還以為是跟同步口譯的模式一樣,想像的是一邊著聽歌詞便將歌詞意思以手語進行翻譯的形式,那還真是錯得離譜。我最初的想像是「日語對應手語」。所以說,我打從一開始就認為只要聽了歌詞後,啪的一下馬上就可以比手語了。
M:我們一開始也不知道 PENKO 桑所進行的「日本手語」跟「日語對應手語」的不同之處。如果用以將日文文章翻譯成英文來比喻的話,「日本手語」就是翻成英文,而「日語對應手語」則類似將日語發音寫做羅馬拼音的。
P:可能跟那個感覺蠻接近的。「日本手語」是從出生起就無法以耳朵接收聲音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而「日語對應手語」則是為後天失聰者、聽力減退者等等,這些人已經掌握了日語作為語言基礎,並將其應用於手語中,以便更好理解與使用日語。 而這次一起演出的團員中也有精通「日本手語」的人,而其中也有表現上偏向「日語對應手語」的人,實際演出時則傳遞出了各種不同的手語。
── 原來如此。畢竟「日本手語」是要表現其內容意義的手語,所以歌詞本身的意義及設定就變得極為重要呢。
P:在使用「日本手語」的時候,可以自由地去使用自己眼前的空間。所以說,從開頭第一句建構出街道的空間,在到第二句時要怎麼去使用這件事,並根據這些考量一邊進行翻譯。所以如果翻譯到後面發現一開始建構出的街道位置好像不太適合的話,也可以採取在另一側重新建構。與其說空間配置上有著很戰略性的考量,不如說是邊想邊做的感覺呢。
── 難怪路樹是從那一個視角來觀察這點,的確有必要去知道其中不同的視角呢。
P:如果(那首歌詞的觀察點)是從一個較遠的地方來看的話,就要去建構一個離自己比較遠的街道場景,反之如果是自己抬頭觀察的話,就要建構一個將自己本人放進街道的狀態。
M:這個討論過程,有點像是如果我是作家的話,「我想要將作品影像化,那這邊這個狀況應該是要用這個 CUT 對吧?」,這感覺像是與影像導演在討論一樣,真的可以說是初體驗。以這層意義來說,除了學習到要將手語翻譯放入現場演出這件事與最初的目地有所差異之外,對於一個寫詞的人而言也是,親身體驗過一次這個轉譯的過程,在創作上的感覺也會隨之改變吧。(野郎的歌曲)就有點像說明極少的電影那種感覺,除了單字量少之外,也盡量去選用一些容易理解的單字去寫詞,不過也因此意外地讓聽眾解釋歌詞的空間變廣了。這可能導致許多需要解釋才能理解的部分,這部份比你預期的還要來得多。
P:你不是還傳了路樹的照片給我嗎?就像這樣的感覺呢。
M:我用 Google 搜尋,打「路樹 街」來搜尋圖片。(笑)
⍝⍝⍝⍝⍝⍝⍝⍝⍝⍝⍝⍝⍝⍝⍝⍝⍝⍝⍝⍝⍝⍝⍝⍝⍝⍝⍝⍝⍝⍝⍝⍝⍝⍝
✦ 差異只在於合聲的媒介是由聲音進行,還是以手語表現
── PENKO 桑在看了 MAKOICHI 君的歌詞後,當時決定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詮釋呢?
P:我擔任手語和翻譯的部分是演出開場的前六首,以及兩首安可曲。當我開始深入解讀某些歌曲時,意識到其中帶有的政治意涵,再以這樣的理解去聽歌時,聽覺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呢。不過,要將其以手語進行翻譯時,特別是在「日本手語」中,必須要像英語一樣清晰地語言化。需要將隱藏在歌詞裡的涵義,用手語的方式明確表現出來。如〈過去有著那些〉(それはかつてあって)這首歌講述著歧視,若用手語表現,就必須得將「過去有過歧視」(差別がかつてあって)用語言明確表現。
M:意義上就會比原本更加強烈呢。第三張專輯的樂曲主題,便是一邊將這樣的主張放進去,一邊讓我們的語言進行共存。因為是將派對歌曲(Party song)與帶有政治性部分混雜在一起呈現,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翻得很艱辛。
P:在〈不被允許的派對〉(無許可のパーティー)一曲中的「放蕩不羈的仇恨 更多被禁止的節奏」的部份,在表現「更多被禁止的」這句時,就是直接表現成:「在夜晚跳舞便會被逮捕」。而在「不被允許的派對 在無法跳舞的街上」(無許可のパーティー 踊れない街で)這段,則是以「雖然沒有得到允許,但我們自己舉行派對,而他們卻說通宵跳舞是違法的這種鬼話」的感覺。不過,實際上到底是由誰禁止的,這邊所涉指的主體是不清楚的。於是將手指比向稍微偏高一點的部分來表現,象徵著是地位比我們還高、且手握權力的人所說的。試著讓大家去思考「那究竟是由誰來禁止的呢?」做了這種安排在手語表現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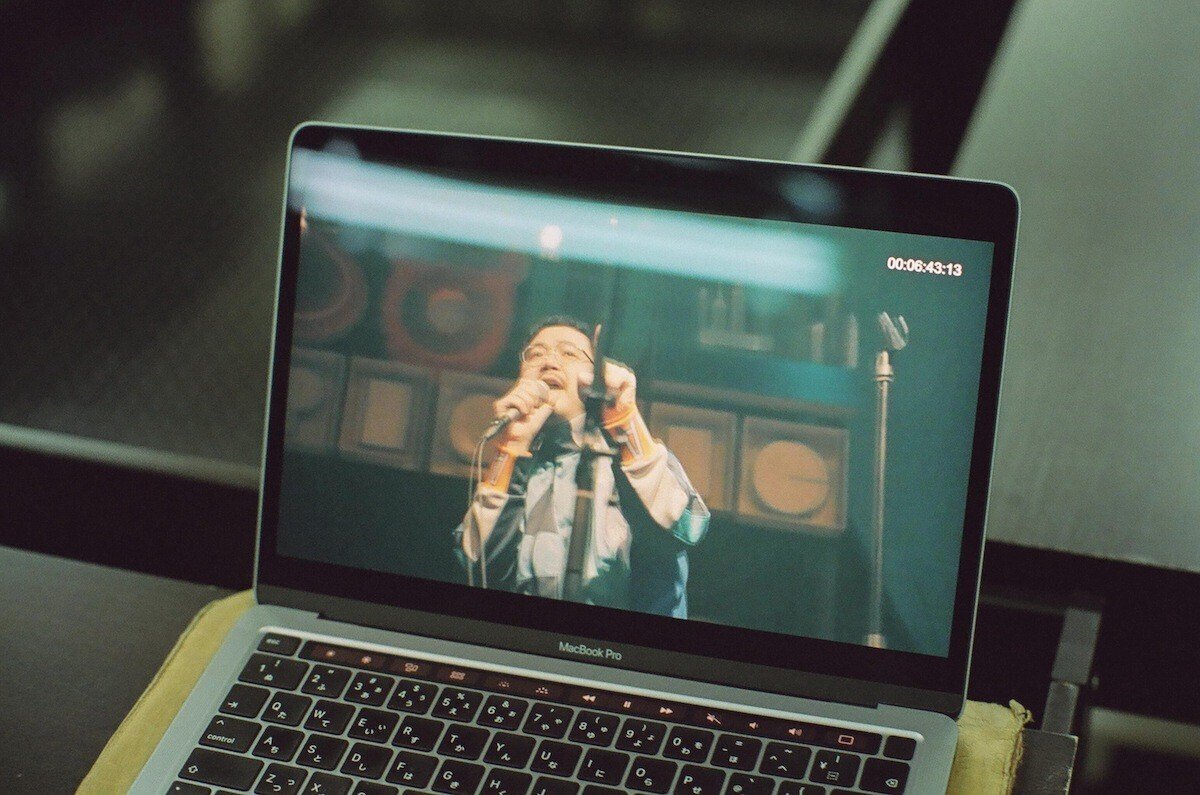
── 真的是深奧地有趣呢。還有其他難以用手語來做翻譯的部分嗎?
P:雖說翻譯的時程大約花了 20 天這麼長,但其中〈平坦的舞池〉(フラットなフロア)這首 B 段唱著:「無論你是誰都沒差 被聚光燈照亮後 我們的肌膚便會呈現顏色斑駁不均」(君が誰でもいいぜ スポットライトに照らされて 僕らの肌はマダラ模様)的地方真的是難到翻不出來。你只要聽過曲子的話,不就可以將其影像化的情況來理解嗎?但是「要將自己腦內浮現出的那個畫面,以手語來表現的話就真的怎樣都做不到」的感覺。真的想了很~久,最後決定採取日本手語中常被使用的戰略,透過重複進行的情況說明,來理解該環境或狀態。所以「無論你是誰都沒差」(君が誰でもいいぜ)就直接翻譯成「與你是誰都沒有任何關係」,而在那之後的部分則放入「由頭頂上照射下來的聚光燈灑落舞池」的狀況說明。然後,再繼續補述「沐浴在聚光燈的照射之下,穿梭行走於舞池間的人群中」的狀況說明。再來還有就是,果然「奏響同一個夜(同じ夜を鳴らす)」的「奏響(鳴らす)」這部分很難。
M:我也嘗試著要說明,但連我自己都解釋得不太清楚呢。
P:我想即便不用說明,我也能夠了解大概是在說什麼,但接著就會想說,那麼我到底要怎麼將它翻成手語呢。
仲原:「奏響同一個夜(同じ夜を鳴らす)」的這段部分,到底是「本身奏響發出聲音的狀態」呢,還是「聽到了那個正在發出聲音的狀態」呢,說白一點就是必須去判斷到底是被動還是主動呢。因為就原本的歌詞來說,就是以兩種都能解釋的形式存在。可以當作實際使用喇叭奏響聲音的演奏者的立場,也可以做為在夜晚將車用喇叭打開聽音樂人的立場。
── 而手語當時是以哪種方式進行解釋了呢?
P:是採取由自己奏響聲音的方向發展,用了「好像有什麼在發出聲音哦」的手語來表現。用了像是由喇叭等擴音器所發出聲音時會使用的手語,將其翻譯成「在夜裡,將音樂,奏響」這樣的感覺。對於手語來說,方向性也十分重要。「是自己發出聲音的狀態」還是「聽到發出的聲音的狀態」。如果是自己發出聲音的話,就會朝著外部的方向來前進;但反之如果是以聽到其他物體發出聲音時,你的感覺會完全改變,方向會產生變化,聲音似乎是從另一個方向傳來的。這樣的方向性,也連同被包含在手語的解釋裡。

M:你提到的這點讓我想起來,我也有一個類似的想法。在我們進行對話的過程中,我注意到歌詞的解釋,可能會因為是來自錄音音源或是現場演唱的預期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像是「與你(君と)」這個詞,在聽音源的時候就會有著像是「面向廣大群眾般傳達的含意」,但在現場演出則會是「更直接地面對眼前觀眾所唱的感覺」。雖說我在舞台上就是就是按照歌詞來唱,但在手語表演中,他們考慮到了錄音和現場演出中演出者情感的差異,並進行了表達。
── 在演出當天,以 PENKO 桑為首的〈TA-net〉的大家也是一同邊舞動身軀,一邊進行手語翻譯的畫面真的是讓人記憶猶新。像那樣在舞台上活動身軀的狀況,在手語翻譯業界也是常有的事嗎?
P:那簡直完全不可理喻(笑)。說「不可理喻」好像是有點太過頭了,不過我想其他的手語翻譯者應該是不太會這樣做。
仲原:實際上一開始我也沒有想到大家會是以那種形式為我們進行演出。不過,在排練的過程中,樂團團員也慢慢開始將手語學了起來,特別是我們的兩位合聲(asuka ando、YAYA 子)開始將自己喜歡的手語加入了舞蹈之中,也因此讓手語使用者開始觀看合聲的動作。在開始理解樂團歌曲的內容後,動作也開始變得活潑生動。
P:我想,這應該是因為在一般進行手語翻譯的狀況下,那種彷彿被釘在原地不動般的狀況可以說是稀鬆平常。
── 對於野郎所演奏的靈魂樂而言,跳舞不就是非常重要的部份嗎?所以反倒讓我以為,有一直提到像是「一起跟著跳起來吧」的對話討論。
M:沒有像那樣的事前討論,畢竟光是我們自己所負責的演奏部分,在彩排上就幾乎已用盡全力了。是在彩排中不時瞥向一旁(手語小隊),才發現「正在跳舞!」這種不經意的程度。所以,與其說是跟其他人一起站在舞台上,不如說是有點像合聲隊裡多了幾個人的感覺,差別只在於合聲的媒介是由聲音進行還是以手語表現。就結果而言,這次樂團的組成擴大,就包含了手語翻譯在其中。
仲原:也請手語翻譯成員穿了相同的服裝(野郎的運動外套),不去區別手語翻譯與樂團的不同,讓大家心中有著「手語翻譯的大家也是團員!」的共識。如果在舞台上加入譯者們的話,恰好是樂團 8 人加上支援 8 人 的男女各半狀態,成了一種「感覺也真的是很野郎呢」的編制呢。

⍝⍝⍝⍝⍝⍝⍝⍝⍝⍝⍝⍝⍝⍝⍝⍝⍝⍝⍝⍝⍝⍝⍝⍝⍝⍝⍝⍝⍝⍝⍝⍝⍝⍝
✦ 即便不去使用,也是人們的自由
── 我認為這場演出的高潮便是安可曲的第一首〈愚蠢的好麻吉〉(アホな友達)中的「默唱」的部分,關於這個想法是從何而來的呢?
M:在演出前進行最終彩排時,就冒出「如果觀眾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比手語的話不是很讚嗎?」的想法。
P:有講過如果先做事前說明的話,大家應該會一起跟著加入吧之類的話。
仲原:在〈愚蠢的好麻吉〉(アホな友達)中的動作是由合聲的兩人做的哦。因為覺得那種感覺很棒,就想說機會難得,不如試著也讓觀眾一起加入吧,是以這種輕鬆心情在做。
M:像「默唱」這個詞,也只是剛好在那個場合偶爾會冒出來而已(笑)。我們不想在演出當天如同教科書生硬地說:「因為今天有手語譯者們在現場,所以請大家把手語記起來」。不想要將其視為一個特殊事件,而是想要更加自然地、更理所當然的狀態來進行演出。到演出當天都感覺有點生硬嗎?雖說好像也有這麼想過。但實際下去做了之後發現,觀眾們在一個比我想像更加自然的氛圍中開心享受,所以感覺可以順利進行下去。
── 變得像是想要把新舞步記起來的感覺呢。
P:那也是因為大家都有跟著我們一起比手語。
M:萬萬沒有想到有天會在推特上看到「愚蠢的好麻吉,可以哭了!」這樣推文(笑)。

── 從演出結束後也過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不是也有收到各式各樣的回饋嗎?
M:特地來看的觀眾有說「就像旁邊有影像在播放的感覺」呢。不過另一方面,因為這次是首次嘗試手語,實際上對聾者們而言是好是壞,像是這類的回饋我們也都不知道。
仲原:實際上有多少人(聾者)看了這場演出,這件事我們也無法得知。
M: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只有我們自己單方面很嗨地覺得「這樣做真是太好了!」是不行的,不想就以這樣做結。並不是說有什麼否定的含意,而是很直接地會有「像這樣的需求有多少呢?」的意見在其中。不過關於這點的需求與否,並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事。公車即便是在空蕩無人的白天也是照常運行,關於其運行的需求與否,不就有點像因為沒人搭乘所以要叫那班公車停駛嗎。當然我們也不是以參與公共事業的身分來玩團的,我們只是將(這次的嘗試)一個選項準備在那,使用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像這次的輪椅區域也是如此。
仲原:因為如果選項都不存在的話,就連想去使用的機會都不會有了呢。
M:雖然知道聾者們的大家去參與音樂相關活動這件事可以感到開心,但比起只有單單我們自己在做這件事做得很開心之外,我想他們一定還有很多想要有像這樣附上手語翻譯去欣賞的音樂人或演出。如果這件事可以慢慢成為一種標配,讓這樣附上手語翻譯的選項漸漸擴展出去的話,那就太好了呢。或許在十幾年之後會有像「(過往像這樣的手語翻譯)只有像是野郎以及一些其他演出者的現場演出中會出現哦」「真的假的?」這種對話出現之類的。
── 對於 PENKO 來說「可以以這樣的方式做到,真是太好了」的結果留下強烈的心情。

P:對啊,像最早第一次要在 the HIATUS 的武道館進行手語翻譯演出時也是。一開始是矢野顯子桑先在推特上發文說「在美國的音樂祭中有附手語翻譯真好啊」,後來矢野小姐向細美(武士)桑說了「我跟你說這個很棒哦,不然你嘗試看看你覺得怎麼樣啊」類似的話,從那個話題開始後才輾轉聯絡到我這邊來。我一直都是抱持著只要有一個能被需要的機會去做的話,我就會想去試試看。
M:當然無論是樂團這邊的費用以及準備時間等等,都需要花上很多時間。大家也不太可能說現在想做就馬上能做到,但如果能有機會的話,我覺得試試看也未嘗不可。總而言之,雖然這次的嘗試中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我認為這次的演出也可以作為某種程度上的成功範例之一。想說或許能稍微讓其他人感受到像是「如果這樣都可以的話,那也來我們試試看吧」的精神。
── 不過我覺得最棒的部分正是因為加入手語,反而讓演出變得更加開心。因為我們並非聾者,所以對於訊息傳遞方式只能透過想像,不過如果有觀眾(是聾者)在其中的話,不就可以知道正在唱的內容了嗎。這種能將音樂傳達至我們觸及不了的地方,讓人羨慕不已。這種事無法僅僅依靠寫一篇報導,讓人了解到這一點。
M:在現場演出中也不是單單只有歌詞的內容,就像現在是誰正在唱這點也是極其重要。手語翻譯的大家也是一邊根據歌詞內容,用各自的風格在同一個舞台上進行表現,這讓我有一種超乎想像中的共同演奏的實感。最近,我們發表了〈與你一起活下去〉(君と生きてく)一曲,雖說當時在寫詞時,完全沒有想過關於手語翻譯的部分,但經過這次的演出,重新審視了一次歌詞,其中「在高牆的另一側」(高い壁の向こうに)寫到的這個「牆」,就會覺得這邊所指的並不是外界,更多是指我們內心無意間築起的那道藩籬。另外〈深夜中的合唱隊〉(真夜中のコーラス隊)說的不就是譯者的大家嗎?因為這段發言感覺太過沉重了,所以我在 MC 上就沒有說了。
── 關於這次的演出,我覺得不論是樂團或是觀眾,都學會了「敲好心靈之門的方式」。雖然實際上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順利敲響聾者們的內心,但能讓大家感受,並以自然地方式去意識到這點,我覺得便是跨出去的第一步。因此,我們只能繼續進行下去,在日本的音樂祭等活動中,讓手語翻譯成為必要的一環,而我認為這次便是做為嘗試的第一步。
M:的確是這樣呢。我也沒有想把這次當成好像已經達成了某個指標性任務般,而是先將這次吸取的經驗做為通往實踐道路上的起點。然而,我當然也不認為因為我們有做這件事情就特別偉大,而沒有將手語導入演出的活動就很差勁怎樣的,關於這點,我想先把話說在前頭。現在也還處於新冠疫情之中(此篇時間點為 2022 年),且大家各自的狀況也都很艱困,而其中也包含有興趣但卻沒有餘力的人。我單純只是想跟大家說,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很推薦去嘗試看看。
仲原:MAKOICHI 當時在 MC 中也有提到,如果有人對於手語翻譯有興趣的話,也請聯絡我們,我們會想全力去協助達成這件事。只是,這件事光是由我們來做,還是有許多觸及不到以及無法達成的部分。因此,我也希望國家將此做為社會保障的一環,致力創造一個人人都能享樂的環境。
── 想說,那不然就以開放資源(open source)的方式來進行吧。而在本篇的最後想問,在明年之後,是否還有機會在野郎的現場演出中再次體驗手語翻譯?
M:關於這點嘛……。想做是想做啦,但就怕(PENKO 桑)他們會不會覺得「怎麼又是這些傢伙啊」呢(笑)。
P:就等您邀請了(笑)。
M:不會有像「不想在穿那個跟他們一樣的運動服了啊」這樣嗎(笑)。
P:不會、不會,沒這種事(笑)。

(完)
この記事が気に入ったらサポートをしてみませんか?
